讓每個鄉村收獲幸福(我與一個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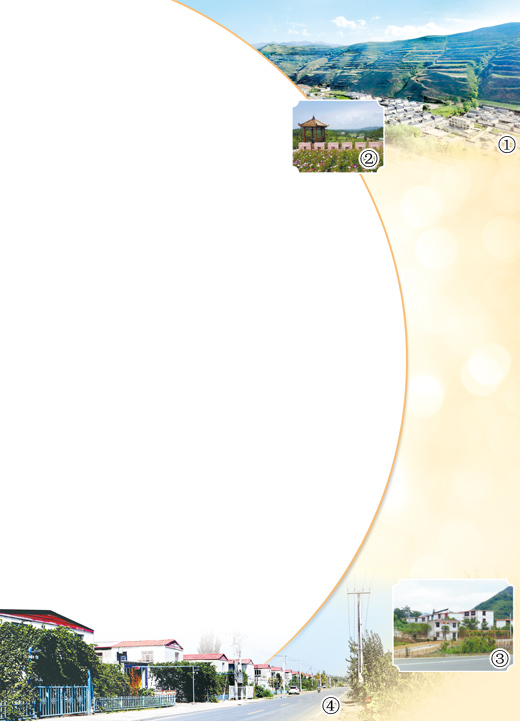 |
圖①:甘肅省池溝村移民安置點。 |
在決勝全面小康、決戰脫貧攻堅的歷史進程中,大批黨員干部下沉一線,進駐鄉村,扎根基層一線,與那里的農民群眾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奮斗在一起,為實現貧困地區的脫貧致富揮灑汗水,貢獻智慧,無怨無悔地拼搏奮斗。同時,他們也在這個過程中,增長了見識,獲得了歷練,與農民群眾的感情更加深厚、真摯。本期大地副刊“我與一個村”特輯邀請了四位駐村第一書記、扶貧工作隊長、下沉干部,講述他們與農民群眾一起,擼起袖子加油干、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動人故事,也分享他們在農村工作中收獲的可貴感悟。
——編 者
四十盞路燈
陳 濤
時常要上山。時常要在高低曲繞的山路上穿行。
有時因為下村工作,有時則只是單純想走一走。記不清有多少次,我站在高高的山路上,長久地望向遠處積雪覆蓋的峰頂,看天空大團大團的白云在山腰草場投下陰影。牛羊滿山坡,悠閑地啃食著青草。還有塊塊長滿金黃油菜花的梯田,層層疊疊向山腳伸展而去。在山腰與山腳還會有或成片或稀散的白色房屋,那是村民的家。有時,我也會在某個時分從村子穿過,進入一條峽谷之中。谷底是一條不寬敞但平坦的石渣路,幾條小溪在兩側草地上流淌,然后再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匯聚,流向我猜不出的遠方。若趕上雨后,山谷安靜,空氣清新,草香絲絲縷縷隨輕風彌漫,沁人心脾。
這就是我任職駐村第一書記的村子。村子共有6個社,其中3個在山上,3個在川里,前些年岷縣地震,山上一些村民的房屋受到影響,縣財政出資將兩個社的村民遷到了山腳下的統一安置點。安置點是我第一次進村時就見到了的,每戶人家都有上下兩層近200平方米的小樓,各類生活設施一應俱全,出門不遠還有配備了體育健身器材的村級文化活動中心與群眾文化廣場。
與山下比起來,山上的條件明顯艱苦些。但一些山民卻不樂意搬下山來,一是在山上住久了,習慣了,二是也圖養牛、養豬的方便。有次黃昏時分,我與夏鎮長驅車去山上一戶村民家中走訪。聽到有人進來,一只小白狗汪汪叫了兩聲,女主人推門出來,站在臺階上大聲跟我們說話。她家的房雖是新房,卻未曾裝修,鋁合金門窗的包裝還未撕掉,蓋房用的磚瓦石塊堆在院內角落,同行的村干部問怎么還沒拾掇拾掇房子,女主人臉便紅了些,說一直沒空,再等一等。
當我們從村民家里出來時,天整個黑下來了,只得借助手機燈光小心翼翼地沿著斜坡走向路邊停靠的車子。
“我們應該安裝一些路燈。”我像是自言自語,亦像是對身旁雖近在咫尺卻難以看清的夏鎮長說。
“是啊!”他拉長了聲音講。
“目前村里有計劃嗎?”
“說不準,目前配套經費還沒到位。”
“要不我跟單位申請一下,我來做吧。”
單位領導聽到我的申請后,立馬便撥付了相關資金。接下來,我與鎮、村的干部們詳細地研究起這件事。那幾天,我們整日在村巷內穿行,測量路燈安放的距離與位置。我們的討論被路過的村民聽到,便笑著要求離自家門口近一些,也有人善意提醒購買的路燈質量要好一些,不要沒幾天就壞掉了。我們笑著說好。大家做事的熱情很高,速度因此也快,等到路燈被卡車運送來后,村民們齊來幫忙,在選好的地方挖坑、澆筑,大約一周光景,40盞路燈便如哨兵般齊刷刷地豎立在這個小山村里。
當最后一盞路燈安好的那個夜晚,我迫不及待地去到山上。遠遠就看到高高的山腰處有一盞燈,燈光溫暖明亮。再一個拐彎,只見那條通往村里的水泥路滿目光亮,這是一條光明之路。
下了車,我輕輕撫摸每一盞路燈,一盞、兩盞、三盞,我在心中默念。有人在村里走動,有幾戶村民正站在門口聊天。他們見到我,跟我打招呼,我也大聲回應他們。一個村民趕著幾頭牛回家,身影在燈光中時而很長,時而極短。而我,抬起頭,望向浩瀚夜空,群星明亮碩大,站立于街口,放眼望去,40盞路燈與低垂的星星交織在一起,光亮灑滿了這個高山的村落。
(作者曾任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池溝村駐村第一書記)
村民有了穩定收入
熊紅久
3年前,當我帶著駐村工作隊員進駐麥蓋提縣恰木古魯克村時,這個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西端的村落,年收入不足2000元,大部分村民還住在幾十年前的舊屋里。
如何精準扶貧?我天天琢磨這件事。
有一天,阿布拉院子里的刨花不小心被火引燃了。好在滅火及時,沒造成大的損失。而這場火災讓我得知,這個村專業干木匠的,有20余家。由于規模小,各自為政,收入并不高,大部分還是建檔立卡貧困戶。何不成立木材合作社,集中優勢資源,打開脫貧突破口?工作隊與村干部很快達成共識。
沒想到,動員木匠們入社就不容易。不是搖頭說不,就是含糊其辭,沒有一個主動報名。村民們私底下說,工作隊待一兩年就走了,只圖個名聲,不會真心干事的。因此,取得群眾信任,成了關鍵一步。
經過分析,我們注意到了阿迪力·熱合曼。他是村里的大戶,七八歲開始學木匠,干了40多年木匠活。住著最好的磚房,擁有最好的設備。他若入社,相信會調動大家的興趣。然而幾次找他,都被婉拒。說大家干活兒習慣不同,想法各異,不好統一,自己單干挺好的。
一周后,阿迪力大兒子結婚。雖然沒收到請柬,我依然決定帶上禮物前去祝賀。叩開阿迪力家的大門,邊吃邊聊,談我們的童年,談成長的經歷,談將來的發展,尤其是談工作隊員們不遠幾千里,到村里來的目的。談我們要攜手并肩,帶領鄉親們一起過上好日子。一直談到我倆雙手緊握,四目潸然。他激動地說:今天,我認你這個兄弟。你說的事,我干了。
之后,我們又得到山東日照援疆指揮部的支持,投資建設廠房,引進具有現代家具生產經驗的廠家。建廠一個月后,我們就從鄰縣簽了加工2000套組合式櫥柜的大單,總價80萬元。不但把全村木匠調動起來了,還聘用了20多名貧困戶做零工。兩個月的生產周期,加班加點,如期交貨。分紅時,入社的每人拿了2萬元,打零工的也掙了5000多元。合作社名聲大噪,阿布拉老漢帶著10戶木匠,主動要求入社。
村民對工作隊的信任,自此建立起來。
入戶走訪時,我們發現許多婦女留守在家,給老人和孩子做飯,沒有穩定收入。根據村里實際,我們引進了以縫紉為主的網袋廠,使婦女們不出村就能入廠打工,每月收入不低于1600元。瑪麗亞姆是村里的貧困戶,兒子不幸車禍去世,自己又癱瘓在床,兒媳婦阿孜古麗只能在家里照顧她和3個未成年的孩子。除了每月600元低保,無其他進項。作為工作隊重點幫扶對象,我們不但找醫保部門幫她報銷了1.6萬元醫藥費,還申請了2萬元的大病救助金。配送了一個輪椅。工作隊員和村干部一起,幫助她家新建了安居房,新修了院墻,連菜園子的蔬菜苗,都幫忙栽好。阿孜古麗被安排進網袋廠上班,既可以照顧家庭,又有了穩定收入。
2020年8月,恰木古魯克村通過了國家對貧困村的退出普查工作,全村高標準脫貧,人均收入超11200元,是3年前的5倍。
我越來越喜歡在村里散步了,清一色的紅磚白墻,筆直的柏油路,每一條街巷都平整干凈,院子門口鮮花綻放。村民們笑意盈盈,他們從勞動中找到了自身的價值,對生活充滿了希望,把日子釀出了蜜意!
(作者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麥蓋提縣恰木古魯克村黨支部第一書記、扶貧工作隊長)
鮮花盛開的石馬
王京川
樂山市井研縣周坡鎮石馬村,曾是個有200戶建檔立卡貧困戶的貧困村。
2015年7月,我以駐村第一書記的身份,與這匹從未謀面的“石馬”相遇。千日駐村記憶,從此無法抹去。翻開我的微信公眾號“周坡石馬駐村日記”,300多篇扶貧記錄、71萬字駐村日記、4000多幅鄉村圖景、數百條暖烘烘的讀者留言,一切仿佛歷歷在目。倏忽,那些浸透著苦與累、笑與淚的點點滴滴,如潮水一般涌進腦海,我仿佛又回到了石馬村。
如今的石馬村,山還是那座山,路已不是那條路。僅僅3年時間,村子的面貌煥然一新。全村完成道路硬化65.5公里,安裝太陽能路燈72組,10個村民小組水、電、光纖全覆蓋,危房改造、易地搬遷100多戶。
如今的石馬村,番茄紅,臍橙黃,李子青,葡萄紫,黃瓜綠,果林郁郁蔥蔥,蓮藕風姿綽約,泥鰍油光水滑,核桃黑白分明,紅薯甜糯可口,獼猴桃綠皮紅心……幾年間,我們抓住石馬村入圍“全省財政支農資金形成資產股權量化改革試點”的機遇,著力打造“山上種水果、山坡建大棚,山下養藕魚”的立體生態農業模式,集體經濟“馬”不停蹄,脫貧“最后一公里”順利打通。
荷塘里,搖曳生姿的荷葉舒展開來,重重疊疊,深深淺淺。荷葉上滾動著水珠,葉柄下游動著小魚。徜徉在曲徑通幽的觀荷棧道,30余畝觀賞荷塘、上百畝蓮藕基地展現在眼前。不遠處的山坡上,是“緣之源”合作社的380畝柑橘園,這里不僅解決了70多名村民的就近務工難題,還將周坡鎮傳統的柑橘美名發揚光大。
微雨,貧困戶李超院里的雞冠花,應該又冒高了一截。10年前,李超因傷致殘。2014年被確定為建檔立卡貧困戶后,縣殘聯為他免費安裝了假肢,工作組和鎮村干部為他爭取了低保。李超每天踩著假肢下地干活,栽了300多棵柑橘樹,一條腿撐起一個家。
貧困戶廖光明家門口的格桑花,今年應該都開過幾茬了吧?前年6月,得知我要離開的消息,這位八旬的老人在一張皺巴巴的面條包裝紙背面,工工整整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謝信。隨后,老人頂著烈日趕到村委會,請他們把感謝信轉交給我。每每重溫這封信,我的心底都會翻涌起股股暖流。
再回石馬村,真是看不完的幸福風景,聽不夠的溫暖話語,說不盡的真心話,聞不夠的花草香。
(作者曾任四川省樂山市井研縣石馬村駐村第一書記)
山村一夜
胡明琳
已是夜里10點多,我正昏昏欲睡,忽然“嘀”的一聲,手機的微信提示音驚醒了我:胡老師,下來玩,我爸和文孃都在!
是小羅發的。小羅是海螺村的環衛工人,專門開垃圾車的,話不多,為人卻很熱忱。他工作十分認真,從不讓一箱垃圾在路邊久放。
王家壩海拔不高但坡度很長,100多戶人家分三地聚居,自然形成上寨、中寨和下寨。我不會開車,每次入戶走訪,從上寨走到下寨,再從下寨爬回上寨,至少需要兩個半小時,即使在綠蔭中穿行,也時常走得大汗淋漓。
那天,我正拖著沉重的雙腿從山腳返程,小羅的垃圾車“嘎”的一聲停在身旁。當時我們還不認識,只因我和他的手臂上都戴著印有“脫貧攻堅決戰隊”的紅袖套,他便下車招呼我。
從那以后,小羅知道我腰椎不好,不能久走久站,便時常開車帶我入戶,或者順道接我回村。
小羅的父親,我喚作“羅哥”,是王家壩的村民組長,與我和文孃組成三人工作小組,共同負責王家壩的脫貧攻堅工作。我們仨彼此包容,取長補短,組里工作開展得很順暢。所以,即便睡意再濃,我都得下樓坐一會兒,不能辜負了他們的盛情。
這時爐火亮堂的院壩里,一幫人見我到來,爭相讓座。主人王哥迎了出來,原來今天是他兒子的大喜日子,難怪人們都到了。王哥是去年脫貧的,他的腿先天殘疾,妻子多年前離開了,留下空空的屋子和一雙兒女。現在好了,樓房修上了,兒子成家了,一顆心踏實下來,王哥的臉上漾滿了笑容。
“胡老師,快來坐!”王哥說著抓了一大把葵花子放我手中。我忙說,甭管我,我喝杯茶就行。
寒暄后,王哥接著忙去了,小羅讓我坐在他旁邊,羅哥遠遠地坐在我對面。院子很大,此時很熱鬧,顯得有點嘈雜,說話聲音低了,有時聽不清,就只能扯著嗓子喊。羅哥說,胡老師,我要為你唱首歌。
當地還保留著唱山歌的習俗,羅哥則是村子里唱山歌的能手,他的山歌曲調非常悠揚。不過現場聊天的聲音大,我到底沒能聽清他唱的啥。小羅一番解釋,我才明白了歌詞的內容:“胡老師呀人不錯,拋家舍業來我組,對人客氣心善良,你是我們的好榜樣。”
這歌詞!這表揚!我一時面紅耳赤。
說實話,我來王家壩的時間不長,沒有農村工作經驗,想孩子時也哭過鼻子,受委屈時也鬧過情緒,因為不熟悉農村生活,還鬧過笑話。比起其他組的駐村干部來說,為老百姓排憂解難的能力還很不足,只是盡力做好每件小事而已。
于是我連忙擺手,別這樣唱,我受之有愧。
人們哈哈笑起來,旁邊的梁哥對大伙兒說,胡老師可以,是個熱心人,見到誰都是笑瞇瞇的。我家兩個小孩不會的作業,我還經常問胡老師呢。
爐火燒得更旺了,人們聊到半夜才漸漸散去。我回到寢室后,還想著剛才的山歌。善良的鄉親們,這是在夸贊我呢,還是在鼓勵我呢?我想,鼓勵的意味恐怕要更濃一些吧。那些細細碎碎的小事,我自己都忘了,他們卻都記在了心里。
大概凌晨3點,我不知不覺進入了夢鄉。夢里,我居然也唱起了山歌:祝村里的鄉親們健康快樂,幸福綿長……
(作者曾在貴州省六盤水市鐘山區海螺村駐村扶貧)
版式設計: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20年10月04日 08 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